由 律 令到 时令秦汉林业立法及森林保护体系变迁
From LLingto Shilingthe Change of Forestry Legislation and Forest Protection System in Qing and Han Dynasties
-
摘要: 从森林资源的有效保护看,秦汉社会以国家为主体的山林保护体系处于不断弱化的历史阶段,对山林护育的 行政保障从先秦时代的律令规制退化为汉代月令等时俗性的约束。对照史籍与出土文献的相关记录,即 使林业资源保护条文的执行也面对得诏书,但挂壁的现实窘境。这一历史性变迁的根源,在于林业立法体系的 弱化。先秦时代较为完备的林官体系逐渐解体,由主要服务于帝室的少府、水衡都尉、将作大匠等零散设置所代 替,且具有重采伐利用而轻于管理护育的特点。Abstract: From the effective protection of forest resources of view, the protection system of forests managed mainly by state during Qin and Han dynasties experienced a historical stage of gradually weakening, and the administrative ensuring of protecting forests was weakened from the L(laws) and Ling(decrees) in the early Qing Dynasty to the Yueling(monthly customary regulations) in Han Dynasty. Comparing the historical records and unearthed documents, the implementation of articles on the protection of forest resources was in real dilemma as even imperial rescript was only hanged on the wall without actual implementation. The root cause of the historical change was the weakening of legislative system on forestry. The relatively complete system of official forestry management was gradually dismissed, and replaced by the unofficial organizations serving royal family, such as Shaofu(in charge of the land, water and handicraft manufacture in Qing Dynasty), Shuihengdouwei(in charge of property, money cast, ship building and the management of water system in Han Dynasty) and Jiangzuodajiang(in Han Dynasty, the same function as Shaofu); moreover it was featured as the huge efforts on logging and harvesting, but little on management and culture.
-
Keywords:
- Qin and Han dynasties /
- forestry legislation /
- forest protection
-
生态学马克思主义将生态危机与“控制自然”相联结,然而在具体观点上,加拿大的北美生态学马克思主义代表人物威廉·莱斯(1939—)与德国的当代生态学马克思主义者瑞尼尔·格伦德曼(1955—)却有不同见解。莱斯认为“控制自然”的意识形态是生态危机产生的根源,他敏锐地发现了理论背后所折射出的现代性危机。具体而言,对自然的控制实质上是对人的控制;科学技术不仅是推动人类进步的手段,也成为满足人类非理性欲望的工具;自然的解放在某种程度上取决于人性的自由与解放。格伦德曼则将生态危机产生的原因归结为人类对自然缺乏有效的控制。他始终坚持马克思的人类中心主义立场,关注人类利益和需要的满足、幸福和解放的实现,宣称控制自然与保护环境并不冲突,人类能掌控自然恰好说明人类能够有效地利用与保护自然。莱斯与格伦德曼在理解“控制自然”思想上的不同侧重,反映出二人对该思想的两条不同阐释路径:现代性批判的阐释路径和马克思主义的人道主义阐释路径,即莱斯从现代性批判的视角阐释“控制自然”思想,格伦德曼基于马克思主义的人道主义阐释“控制自然”思想。“控制自然”思想的两条不同阐释路径不仅深化了我们对资本主义社会生态问题的理解,也给予我国生态文明建设以理论上的启示。
一. 莱斯对“控制自然”思想的现代性批判的阐释路径
对现代性问题的探索经历了由纯粹哲学层面的解读到历史辩证法的审视的转变。对现代性问题作历史辩证法的审视,离不开从“解构”的意义上理解现代性,对现代价值观念和现代性问题进行批判。莱斯不仅通过“控制自然”思想分析资本主义社会的生态危机,还揭示了“控制自然”观念作为一种意识形态在资本主义社会的确立、科学技术对人的控制以及资本主义社会存在的合法性问题,简言之,莱斯是从现代性批判的视角阐释“控制自然”思想。
首先,莱斯认为“控制自然”思想在资本主义社会表现为一种意识形态。他认为“控制自然”思想的历史演变共经历了四个时期:神话和宗教时期、文艺复兴时期、17世纪以及17世纪以后到现代。神话和宗教时期是“控制自然”思想的萌芽时期,这一时期,人们或者既渴求又畏惧自然,或者出于对《圣经》的信奉认为人有控制自然的权力,在基督教自然观的影响下,人类获得了控制自然的合理性;文艺复兴时期,哲学家重新评价了人的形象和地位,将人的力量等同于神的力量,由此,“控制自然”思想得到了理论层面的论证;进入17世纪,培根从哲学世界观上确立了人控制自然的观念,他认为科学技术是一种独立的存在,人类通过科学技术手段利用自然以满足人类的发展;17世纪以后到现代,“控制自然”思想已经深入人心,即“通过科学和技术征服自然的观念,在17世纪以后日益成为一种不证自明的东西”[1]71。
莱斯认为,当前的资本主义社会符合上述的第四个时期,其特征表现为“控制自然”思想成为统治集团进行社会统治的意识形态,这种思想虽然打破了自然主义观念对人的束缚,但其在社会的非理性支配下成了控制人的工具,使个体丧失了主体性,接受着资本主义“同一性”意识形态的支配。现代性的内在矛盾是由同一性引起的,当“控制自然”思想成为资本主义社会的“同一性”意识形态时,人们便非理性地运用科学技术,毁灭科学技术的合理性,掠夺式地开发自然界。沿着这样一种思路,莱斯对自然危机产生的思想根源展开了批判,在他看来,人将自然视为纯粹对象的观念是对自然内在价值的漠视,人若不尊重自然,只是不断向自然索取,生态危机的爆发就会在所难免。西奥多·阿多诺曾指出,“同一性是所有意识形态的原初形式”[2]3,它会压制所有的矛盾,资本主义社会受这种意识形态的控制,“自觉地与传统决裂,千方百计地去追求推翻一切‘自然主义’的思维和行为方式,把为了满足人类的物质需求和发展生产力作为压倒一切的任务”[3]27,这会使工具理性与实用主义思维方式愈演愈烈,其最终结果就是自然与人的双重异化。
其次,莱斯认为控制自然的实质是对人的控制。在他看来,“控制自然”与“控制人”具有内在的联系。一方面,“控制自然”看似意味着人与自然之间矛盾的加剧,实则暗含着人与人之间的冲突与斗争,“控制自然”表明某一利益集团掌控着某种范围内的资源,他们凭借所占有的自然资源,可以实现对其他人的控制。另一方面,人的非理性欲望使得“控制自然”必然转向控制人本身。莱斯说过:“控制自然的任务应当理解为把人的欲望的非理性和破坏性方面置于控制之下。这种努力的成功将是自然的解放——即人性的解放:人类在和平中自由享受它的丰富智慧的成果。” [1]168人的非理性欲望如同霍克海默所说的主观理性,它以实用主义为主要表达形式,将目的与手段的地位相颠倒,以自然为载体追求自身利益的满足,“无限地统治自然界,把宇宙变为一个可以无限猎取的领域,是数千年来人们的梦想。这就是男人社会中,人们思想上所追求的目标。这就是男人引以为豪的理性的意义”[4]235。当利益集团完全支配了自然,他们会将“控制自然”观念纳入现代性价值体系之中,从而达到控制人的目的。
现代性的不断推进,使人的存在方式从物的依赖性转变为以物的依赖性为基础的人的独立性。黑格尔曾在市民社会理论中提到,个体的生产及利益的满足离不开他者,他认为:“每一个特殊的人都是通过他人的中介,同时也无条件地通过普遍性的形式的中介,而肯定自己并得到满足。”[5]97马克思在讨论人的发展时,也强调了社会关系的重要性。现代性的发展越来越凸显出人之于人的作用,但资本逻辑却暴露了现代性在这一环的缺失。资本逻辑追求利益最大化,人与人之间的关系被简单地划分为利益关系,工人依附于资本家,受制于资本的驱使,这与马克思的“真正的共同体”所倡导的平等性原则相悖。莱斯认为对人的控制正是资本逻辑使然,为此他提出将人的非理性欲望置于控制下,以人性的解放对抗“控制自然”思想,通过对社会制度进行改造以实现从控制自然向解放自然观念的转变,即“从道德进步来考虑,它(指‘控制自然’)将更有力地表明我们所面临的最迫切的挑战,不是征服外部自然、月球和外层空间,而是发展能够负责任地使用现成的技术手段来提高生活的能力(这种能力广泛地分散在社会中每一个人身上),以及培养和保护这种能力的社会制度”[1]169-170。
最后,莱斯认为科学技术成为控制人的工具。莱斯立足于法兰克福学派的理论,将科学技术视为一种新的统治形式,这表现在:对自然的控制和对人的控制所依靠的手段都是科学技术,“按照流行的观点,征服自然被看做是人对自然权力的扩张,科学和技术是作为这种趋势的工具,目的是满足物质需要。这样实行的结果,对自然的控制不可避免地转变为对人的控制以及社会冲突的加剧”[1]169。不仅如此,莱斯认为科学技术对控制自然程度的加深,实际上也是对人的控制的加深,正如他所说的:“对人的劳动和剥削的强度直接依据于控制外部自然所达到的程度。这里的决定性一步是工业社会的到来:机器和工厂系统扩大了劳动生产力,从而扩大了对它的剥削的可能程度。”[1]138
科学技术与理性是推动现代性发展的动力,但过分迷信理性会使理性走向其反面,从而催生现代性的危机。莱斯并不否定科学技术的重要作用,但他认为科学技术的非理性运用是导致资本主义社会“控制人”现象出现的关键。在莱斯看来,资本主义社会处于一种“合法性”危机之下,一方面,科学技术的不断进步和工具理性的愈演愈烈为资产阶级创造了前所未有的物质利益,资产阶级在此基础上继续加深对人的控制;另一方面,在工具理性的驱使下,自然本身的负担日益加重,生态问题也日益频发。基于一种现代性批判的阐释路径,莱斯主张以正确的态度对待理性与科学技术。
莱斯从现代性批判的视角阐释“控制自然”思想,该阐释路径兼具理论贡献与理论局限。就其理论贡献而言,首先,诠释了“控制自然”思想所蕴含的主体的能动性。在莱斯看来,人类是地球上唯一具有精神属性的存在物,拥有着对地球生命的派生统治权,“人立于自然之外并且公平地行使一种对自然界统治权的思想就成了统治西方文明伦理意识的学说的一个突出特征”[1]28。“控制自然”思想体现出“崇尚科学、破除迷信,鼓励人们树立改变生存条件的信心和决心” [6]68 ,这与文艺复兴运动高扬人的主体性的思想主张相契合。其次,对科学技术进行了辩证的分析。莱斯认为科学技术本身具有一种价值中立性,但在实际层面上它既能推动人类社会的进步,也能给生态环境带来消极影响。他对科学技术的辩证分析,推动了生态学马克思主义理论的发展。最后,揭示了“控制自然”思想背后的资本主义生态危机是一场现代性危机。资本主义社会对科学技术进行非理性运用,将“科学理性”等同于“技术理性”,以粗暴的态度开采利用自然以满足资本的需要,激化了人与自然的矛盾。为了使社会成员认同自己的统治秩序,资本主义将自身的意识形态灌输给他们,压制了个体的自由意志。因而,科学技术的非理性运用、理性的扭曲、自由意志的丧失不仅是生态危机产生的原因,更是资本主义现代性危机的体现,生态危机在某种程度上就是一场现代性危机。然而,莱斯现代性批判的阐释路径的理论局限也较为明显,其一,莱斯对生态危机根源的认识不够深入。莱斯将生态危机产生的根源归结为“控制自然”思想,很显然忽视了社会意识背后的社会存在,“控制自然”思想是在资本主义制度下产生的,生态危机的产生正是资本主义制度所造成的。其二,莱斯关于生态危机的解决方案具有一种理想性。莱斯夸大了伦理道德的作用,试图依赖于意识形态即伦理道德约束力解决生态危机,并没有触及生态危机的本质根源,不可避免地带有一种理想主义色彩。
二. 格伦德曼对“控制自然”思想的马克思主义的人道主义阐释路径
从普遍的意义上来讲,人道主义在当下是全人类共同的价值取向,但从马克思主义理论的视阈来分析,资产阶级是从抽象的意义上谈论人道主义,并不是彻底的人道主义。格伦德曼始终坚持捍卫马克思的人类中心主义立场,基于历史唯物主义从人的需要出发看待对自然的控制,他是在马克思主义的人道主义立场上阐释“控制自然”思想。
第一,格伦德曼将人对自然的有效控制理解为人对自然“人道的占有”。通常来讲,人控制自然指的是人凌驾于自然之上,将自然作为满足自身利益需要的纯粹对象。格伦德曼在对“控制”一词的理解上展现了自己的独到之处,他将控制看作一门艺术,特指人通过有意识的活动,合理地开发与利用自然。在他看来,生态危机并不是如莱斯所分析的由“控制自然”的观念催生的,相反,它的产生归因于人对自然缺乏有效的控制。他认为正如音乐家可以熟练地控制乐器演奏出美妙的音乐,人类有效地控制自然便是对自然最大的保护,因为有效地控制自然意味着人类以尊重自然规律作为利用自然的前提,这样便避免了对自然的破坏。不仅如此,格伦德曼把人对自然的有效控制理解为人对自然“人道的占有”,所谓“人道的占有”,即把自然界改造成符合人的本质的环境世界,也就是说,人道对应的是人的需要的满足和人的利益的实现。
在生态问题上存在生态中心主义、人类中心主义等不同价值立场,生态中心主义重视整个生态系统以及生物圈内各物种的价值,认为人类相对于其他存在物来说并不具有特殊的权利,每个存在物都有其不依赖于人的内在价值,道德关怀的对象应该由人扩大到自然界。人类中心主义则侧重于强调人类需要的满足,认为在人与自然的价值关系中人是主体,要将人类的生存和发展作为最高目标,应该“从整个社会的长远和整体利益出发,维持生态系统的平衡,维持自然界物种的多样性和丰富性”[7]76-77。格伦德曼吸取了马克思“支配自然”的思想,他坚持马克思对技术的辩证分析与运用,主张积极发挥技术的经济作用与生态效用,进而实现对自然“人道的占有”。格伦德曼坚持马克思的人道主义立场,以人为根本出发点考察人与自然的关系。他认为:“扩大工具主义价值观,通过增加科学、美学和伦理因素,基于人的需求和利益,而不是狭隘的、短视的经济偏好,达到可从人类的立场评估生态问题和可能的解决方案。”[8]187 在他看来,“支配的概念只有与支配主体的利益与需要相关时才有意义,马克思既主张在共产主义条件下支配自然,又批判资本主义社会对自然的支配,这显然是以人的利益为参照辩证地看待支配自然”[9]3。他所谓“人对自然的有效控制是人对自然‘人道的占有’”侧重于强调在利用自然的基础上满足人的利益,控制自然在他那里是实现人的目的的重要手段。此外,他将“控制自然”与人类的利益相挂钩,强调只有充分实现人类利益的控制自然才称得上真正的控制自然,这正如他在揭示马克思“支配自然”思想时所说,“对马克思而言,支配观念仅涉及利益和需求”[8]92。
第二,格伦德曼将“控制自然”与环境保护的统一理解为人类利益与自然利益的统一。在大多数生态学马克思主义理论家看来,控制自然意味着奴役自然,它是将技术理性作用于自然之上,对自然资源进行肆意地开采,因而,他们认为控制自然与环境保护相背离。格伦德曼并不认同这种观点,他觉得“当前的生态危机正是由于支配自然的不足所造成的”[8]92,假如人类可以有效地控制自然,生态危机就不会出现。正如前文提到的,控制自然是以尊重自然规律为前提的,它的结果势必利于对自然的保护。从某种程度上说,格伦德曼所讲的控制自然等价于环境保护,二者的统一也是一种必然。
在“控制自然”与环境保护实现统一后,人类利益与自然利益实现了统一。格伦德曼坚持人类中心主义,他所坚持的人类中心主义有别于近代人类中心主义。近代人类中心主义是一种具有资本主义形式的传统的人类中心主义,其囿于资本主义制度的框架,剔除了理性本身固有的关于价值的思考,将理性直接等同于经济理性,强调以追求经济效益为根本出发点;将价值简化为“经济价值”,执着于对抽象的交换价值的追求,忽略了价值本身的科学维度;秉持人类沙文主义立场,将社会的进步等同于技术的进步,将技术看作人类征服自然的工具,而将自然视为维护资本主义生产条件的工具。格伦德曼所坚持的人类中心主义兼具对自然内在价值和人的价值的强调。一方面,他并不否认自然之于人类发展的意义,正因如此,他以对自然规律的遵循作为控制自然的首要前提。格伦德曼认可马克思对人与自然关系的论述,他认为人依赖于自然界,自然具有内在价值,它为人类源源不断地提供生存所必需的空气、阳光、水等资源,人类是在满足自身自然需要的基础上才从事社会交往的。另一方面,格伦德曼认为人类的发展是最终的目的,他与马克思的价值立场保持一致,即在控制自然的基础上致力于实现人类的最大利益。格伦德曼曾提出“自然的繁荣”和“人类的繁荣”,同时也认为,“如果人类想要繁荣,这两个因素都必须繁荣”[8]63。自然利益和人类利益在他这里真正实现了统一。
第三,格伦德曼将能否增进人类福祉、满足人类需要作为“控制自然”的预先假定的目的。格伦德曼是马克思人类中心主义立场的坚定支持者,他批判生态中心主义,认为生态中心主义虽标榜以“生物圈平等主义”为立场,尊重生态系统中每一物种的价值,但其并未超越近代二元对立的机械论世界观,在本质上是一种人与自然对立的二元论思维范式。并且,生态中心主义理论具有一种抽象性,缺乏一种现实关照力。认为人类中心主义“控制自然”思想引发生态危机的观点,实际上是将人类中心主义作泛化的理解,将其与近代人类中心主义混为一谈。近代人类中心主义的价值观“具有‘人类统治主义’‘人类沙文主义’和‘物种歧视主义’的缺陷”[10]60造成了人与自然关系的根本对立。马克思的人类中心主义是对近代人类中心主义和生态中心主义的超越,是一种现代人类中心主义。它以历史唯物主义为前提,以对资本主义制度的批判为核心,以人的整体利益为宗旨,真正符合人类的价值取向,这里所说的“人”是真正“现实的”“具体的”人。它不仅重视尊重自然,还强调在尊重自然规律、利用自然的基础上,满足人类的真实需要。格伦德曼坚持并重新阐释了马克思的人类中心主义价值观,他将人类福祉、人类需要与“控制自然”相结合,把马克思的人类中心主义价值观发展为一种现代的、使人与自然处于良性互动之中的人类中心主义价值观。前文讲到,格伦德曼将能否称为“控制”理解为是否促进了人类的利益,这里暗含了一个预先假定的目的,即人是目的,人的需求、人的幸福和发展是“控制自然”的最终诉求,他明确界定了“控制自然”的目的在于实现人自身的利益。以人为基准去评估生态问题,它的方向定然是正确的,“以人类为立足点来评估生态问题、寻求解决方案成为可能”[8]57。
格伦德曼从马克思主义的人道主义出发阐释“控制自然”思想,透过这一价值立场,其理论贡献与理论局限也得以展现。理论贡献表现在:第一,它破除了对“控制自然”的理论误读。格伦德曼指出“控制自然”思想不仅不会造成生态危机,反而有助于解决生态危机。一方面,生态危机的产生归因于多方因素的综合影响,观念角度的“控制自然”思想只是危机产生的原因之一;另一方面,格伦德曼所讲的“控制自然”是在马克思历史唯物主义框架下的,它强调在尊重自然规律的基础上保护自然。第二,格伦德曼通过对“控制自然”思想的阐释驳斥了关于马克思“生态空场”的理论认知。格伦德曼坚持捍卫马克思的技术观、自然观以及人类中心主义立场,他认为,人类与自然和谐共生是马克思人类中心主义价值观的基本特性,这一方面表现在人对自然具有一种生存依赖,另一方面表现在自然是物质财富的源泉。格伦德曼以历史唯物主义为前提,从人类历史发展和理性的角度看待技术和对自然的控制,他指出,马克思不仅强调了人与自然的有机联系,还基于历史唯物主义实现了自然、历史与人类实践之间的统一,强调以实践为中介的人与自然的辩证法,反对肆意破坏自然,绝非存在一种“生态空场”。
然而,格伦德曼对“控制自然”思想的阐释也存在理论局限。第一,格伦德曼过分夸大了人的主观能动性。他在分析人与自然的关系时,借用了人对小提琴的操纵,这是对人的主体性的标榜,但忽视了自然本身的规律和客观性。第二,格伦德曼弱化了对资本主义制度批判的实践性。资本主义社会生态危机产生的根源在于资本主义制度本身。资本主义制度和以资本为逻辑的生产方式使资本主义为了发展自己,掠夺性地使用自然资源,破坏了人与自然之间的物质能量交换关系。随着资本主义不断强调资本积累和价值增殖,个体对自然的态度发生了改变,即“自然的用处和观念随着生产方式的改变而改变。在资本主义制度下,不像以往的生产方式,改变自然是为了获得交换价值和使用价值,因而自然往往以商品的形式被客体化”[11]156。在格伦德曼看来,马克思对资本主义制度的批判及其所提出的资本主义危机的解决方案,并不能在真正意义上破除资本主义生态危机,他质疑社会主义对生态危机的解决,进而弱化了对资本主义制度批判的实践性。
三. 关于“控制自然”思想的不同阐释路径对我国生态文明建设的理论启示
莱斯与格伦德曼对“控制自然”思想的阐释,为我们理解“控制自然”提供了不同的角度。他们从正反两个角度诠释了自己的生态立场和主张,展现了生态学马克思主义理论家各自的理论特色。当下,生态问题是全人类所面对的共同难题,面对日益严重的生态危机,我国也在积极构建社会主义生态文明理论。莱斯和格伦德曼对“控制自然”思想的阐释,在人与自然关系、科学技术与人类社会关系等方面为我国的生态文明建设提供了必要的理论启示。
首先,深化对人与自然关系的认识。从哲学诞生起,人与自然的关系问题就成为研究对象,时至今日,这一问题已成为影响人类生存与发展的基本问题。马克思在《1844年经济学哲学手稿》《德意志意识形态》《资本论》等著作中,对人与自然的辩证统一关系作了详细的阐述,他认为人与自然的关系包含以下几点:其一,人是自然界的产物,人的生存和发展离不开自然界。“自然界,就它自身不是人的身体而言,是人的无机的身体。人靠自然界生活。”[12]45其二,人始终需要与自然进行物质和能量的交换以满足自身的生存和发展。其中,劳动是进行这一交换的条件,人类进行劳动就是利用自然资源改造自身,待自身发展后,又将主观能动性作用于自然。其三,人类与自然在实践的基础上实现统一。人一方面受制于自然规律,另一方面以尊重自然规律为前提,通过实践活动积极地改造自然。在莱斯看来,科学技术是控制自然的工具,人的需要是“控制自然”思想产生的土壤,他始终是在二元对立的框架下审视人与自然的关系。格伦德曼证明了“控制自然”思想中包含的按客观规律开发保护自然的意蕴,强调对自然本身和自然内在价值的尊重。当下,我国在构建生态文明理论的过程中,应该深化对人与自然关系的认识,重新思考人与自然的辩证统一关系,摒弃在人与自然关系上主客二分的思维范式。一是要深刻认识到人与自然是生命共同体。人类是自然界的重要组成部分,自然界先于人类而存在,人因自然而生,人与自然是一种共生关系。人与自然的和谐共生关系不仅是我们对人与自然关系的新理解,也是推动生态文明建设的新方向。在新时代,我们要全面把握我国生态文明建设面临的形势和挑战,“努力建设人与自然和谐共生的现代化”[13]。二是应该坚持有机论的世界观。强调人与自然的关系是一种相互联系、相互作用和相互影响的关系。在利用和改造自然的过程中,应该尊重自然的本性,尊重自然的内在价值,不逾越于自然之上。三是应该统筹人与自然的共同发展。人类活动应遵循自然环境的客观规律,科学化解人与自然的矛盾。努力践行保护自然的宗旨,做到敬畏自然、尊重自然、顺应自然、保护自然,积极倡导人与自然和谐共生的生态理念,谋求人与自然的共同发展。
其次,正确把握科学技术与人类社会的内在关系。从理论维度来讲,人类社会的发展得益于现代性的不断推进,其中,理性与科学是助力现代性的两股力量。马克思曾盛赞生产力与大工业对人类进步的贡献,科学技术有力地推动了个体与整个社会的发展。现代性包含审美现代性和启蒙现代性,启蒙现代性将现代性的基础归结于理性,强调基于科学技术的技术理性在社会中发挥作用,它虽然反映了整个社会现代化水平的攀升,但也暴露出技术理性对个体与社会的支配。在科学技术发展的背后,潜藏着诸如资本扩张、文化工业、时空压缩、都市化、风险社会乃至生态破坏等一系列问题。莱斯认为,科学技术本身是中立的,科学技术在人类生活中扮演什么样的角色,关键取决于人们使用科学技术的方式。我国在生态文明建设中离不开科学技术的支持,合理运用科学技术的首要前提便是在理论层面上正确认识科学技术,辩证地看待科学技术。从实践维度上讲,科学技术是社会进步的现实驱动力,我国在较早时期就已经认识到“科技是第一生产力”。人类从原始文明发展到农业文明、工业文明,再发展到当前的生态文明,在这个过程中生产力起到了重要作用。生产力与科学技术紧密相连,有了先进的科学技术,人类不断进行创新,不断更新生产方式;没有先进的科学技术,人类的发展将面临考验。但科学技术的不合理运用往往会导致社会问题的出现,诸如生态问题。诚如资本主义制度与科学技术相结合的时候,生态原则被他们遗忘,“绝没有先验的理由可以保证生态技术将会以生态原则为基础的——除非各个资本或产业相信那是有利可图的,或者生态运动和环境立法逼迫他们那样去做”[14]326,资本主义注定与生态原则背道而驰。我国在生态文明建设中,应该合理理性地使用科学技术,发挥科学技术在促进社会进步、加强生态保护、增强人民福祉等方面的积极作用,积极利用先进的技术减少人类活动对自然的破坏,提高资源的重复利用率和使用效率,并立足于前沿技术开发新能源和可再生资源。将科技创新作为解决生态危机的战略举措,增加财政对科研的投入,为科技创新提供物质保障,建立科技创新激励机制,提高技术研发的积极性。此外,在意识形态层面呼吁人们合理地使用技术,不标榜技术至上,也不凌驾于技术之上,规避科学技术的负面影响。
最后,立足价值观维度和制度维度,推进我国生态文明建设。生态文明建设是一项庞大的工程,也是一项长久的工程,“是关乎中华民族永续发展的根本大计”[15]51,我国的生态文明建设应统筹好价值观维度和制度维度。在价值观层面,倡导全民树立环境保护理念和正确的需要观、消费观、幸福观。莱斯曾坦言:“科学本身并不是造成环境问题的根本原因,而是存在于社会当中的意识形态,现代科学仅仅是作为一种工具的存在。所以,造成生态危机的是人们要征服自然的观念。”[1]2那么,我国当前的生态文明建设要将转变人们的思想观念作为基本前提。我们应该深刻认识到,生态意识的缺乏是造成生态问题的思想根源,传统的人类中心主义的生态价值观念不适应当下的生态文明建设。我国应积极号召全民树立环境保护的理念,利用多种途径和方式进行生态教育,使生态意识深入每一个公民心中,实现价值观层面的自我意识革命,最终使更多人积极践行环保义务。此外,引导公民从真实的需要出发进行消费,避免因虚假需要而引发异化消费,让人们明白幸福不是沉浸于无止境的消费之中,而是通过自由自觉的劳动满足自身的真实需要。在制度层面,我国应制定严格的环境保护法律,依靠法律的强制力约束人们的行为,根据生态环境出现的新问题对法律进行完善。深化生态文明制度体系,对自然资源的使用权制度、生态补偿制度、生态考评体制、自然资源管理体制进行变革以顺应时代的变化。优化完善相关的生态保护法和生态保护条例,加大生态环境司法保护力度。建立健全公众、网络、媒体等多渠道的执法监督体系,将工作真正落实到具体的责任人,使其积极履行自身职责。此外,针对发达国家对发展中国家的污染转嫁和自然资源掠夺,我国应该坚决捍卫本国的环境权,倡导建立国际政治新秩序,打破资本的霸权及其对国际秩序的掌控。
计量
- 文章访问数: 786
- HTML全文浏览量: 42
- PDF下载量: 148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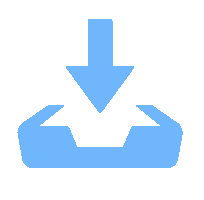 下载:
下载: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