The Ecological Consciousness and Ecological Protection of Hanjiang River Watershed from the Qing Dynasty to the Republic of China (1644—1949)
-
摘要: 清至民国时期, 韩江流域森林生态系统遭到严重破坏, 造成了水土流失、江河淤塞以及水患灾害频仍。对此, 部分地方官吏、乡绅、有识之士, 乃至地方民众开始反思森林与灾害之间的关系, 生态意识逐渐增强。为此, 人们也开始采取了一些保护生态环境的措施, 主要从两个方面着手:一是从保护林木的角度出发, 订立乡规民约, 立碑护林, 制止人们的滥砍滥伐行为; 二是从植树造林着手, 提倡和进行造林的实践, 从根本上解决森林大面积破坏的问题。Abstract: From the Qing Dynasty to the Republic of China, the forest ecosystem of Hanjiang River watershed was seriously damaged, resulting in soil erosion, river siltation and flooding disasters frequently occurring. Regarding this, some local officials, gentry, men of insight and the villagers began to introspect the relationship between forest and those natural disasters, and concurrently their ecological consciousness was gradually enhanced. Therefore, some measures to protect the ecological environment were initiated, mainly from two aspects: 1) the rural regulations to stop deforestation behavior of people from the perspective of the forest protection were formulated; 2) afforestation from trees planting was advocated to fundamentally solve the problems concerning large-scale forest destruction.
-
韩江流域地处粤东、闽西南, 为广东除珠江流域以外的第二大流域, 流域范围横跨闽粤两省, 大部分流域面积都在广东境内, 主要流经今梅州、潮州、揭阳和汕头四地市①。清至民国时期的韩江流域, 随着人口快速增长, 垦殖日益加剧, 人地矛盾日益突出, 人们开始大面积的毁林开荒, 出现了大量的过度砍伐林木的现象, 导致韩江流域森林植被遭到了毁灭性的破坏。学界有关韩江流域生态史的研究并不多, 有的学者从历史地理学角度讨论韩江流域湖泊、渡口的生态环境变迁, 也有学者从社会史的视角考察韩江流域地方宗族与山林开发、环境保护之间的关系[1]。本文以韩江流域为研究对象, 充分利用和挖掘地方志、农林调查报告等文献, 讨论清至民国时期韩江流域人们的森林生态意识与森林生态保护。
① 韩江流域干流发源于紫金县七星崠, 北称梅江, 北东向流至大埔三河坝与汀江(发源于福建长汀马木山)汇合后始称韩江, 此后折向南流, 至潮安进入韩江三角洲, 分为东溪、西溪、北溪, 经汕头市各入海口注入南海。主要支流有汀江、五华水、宁江、石窟河和梅潭河。文中所指的韩江流域, 清代为潮州府和嘉应州所辖, 民国时期主要包括汕头、潮安、潮阳、揭阳、普宁、澄海、丰顺、南澳、大埔、饶平、惠来、梅县、兴宁、平远、蕉岭、五华等地区。
一. 人们的森林生态意识
清至民国时期, 面对韩江流域日益严重的水土流失、水患灾害等生态问题, 部分地方官吏、有识之士, 乃至地方民众, 开始重新认识森林与灾害之间的关系, 生态意识逐渐增强。
一 对森林保持水土作用的认识
现代林业科学表明, 森林是地球生态系统的核心, 它具有保持水土等诸多方面的生态功能。我国早在先秦时期就产生了对森林保持水土作用认识的萌芽, 汉晋时期对此有了初步的认识, 唐宋时期有了明确的认识, 明清时期产生了普遍的认识[2]。
清至民国时期的韩江流域, 部分地方官吏和一些有识之士, 已经普遍意识到了森林具有保持水土的作用, 对森林与水土保持之间的关系有了较为明确和科学的认识。康熙《埔阳志》记载, 大埔茶山, “建邑初, 草木森浓, 旺气攸聚”, 其后“不禁樵采, 听其濯濯, 官民两不利焉”, 森林遭到破坏, 进而得出认识:“盖斩木则童、刈草流潦、控葬戕脉、崩裂之患因之, 此形家大忌也。”[3]乾隆《大埔县志》也记载, 大埔“乃生齿繁, 而樵采者众, 地力僻而烧畲者多, 山濯濯童矣”, 当遇到大雨时, 就会导致“百道流潦, 泥沙崩塌, 淤塞沟渠, 涨溢为患, 堤易荡决, 田被淹浸”[4]。清末民初兴宁的刘鉴仁在《兴宁治水计划》中指出, 由于兴宁“沿河童山赤土, 久患崩颓”, 森林遭到破坏, 导致了“各处崩塌, 沙泥交汇奔注”, 从而“遂致河底日高, 容水日少”, 以至兴宁“每遇春夏盛涨, 不必十日淫雨, 而沿河居民已罹溃决四溢之灾”[5]。民国的王延康在分析潮州水患原因时, 也意识到了森林在保持水土中的作用。他在《筹浚潮州韩江刍议》中指出:“潮之州, 大海在其南, 自古在昔, 河道畅流, 生其地者安居乐业, 不闻水患也。明季清初时有所闻, 近数十年, 则几于无年无之, 其故何哉?西北森林斫伐殆尽, 土失所护, 流而为砂, 砂土既积, 溪为之浅, 一也。塭田填塞, 海口狭隘, 河流迟滞, 涨水益高, 二也。有此二者, 日甚一日, 数十年来其患尤深。”[6]
森林的破坏不仅仅导致水土的流失, 引发水患, 而且还使得农田肥力因此变劣, 影响农业生产。林纯煦等在《兴宁县农业调查报告》中指出:“盖该县山岭殆皆荒废, 稍生苗木, 辄被樵采, 山林无森林之庇护, 自易崩毁。每当春雨淋漓之际, 山岭砂坭, 遂倾泻田畴, 河道固为之淤塞, 而农田肥料亦因以变劣。”[7]森林的破坏, 致使泥沙随水而下, 在河道平缓处沉积下来, 久而久之就容易出现江河的淤塞, 河床的升高。谢雪影在《潮梅现象》就指出:“推其原故, 实由于沿江两岸居民, 既不广造森林, 益以斧斤不时, 甚至放火焚山, 以取草灰, 遂使牛山濯濯, 无苔藓落叶以资补覆。裸露既久, 土垠大半失其凝集力。遇降雨之际, 即直接打击地面, 奔流冲激, 一泻而下, 挟泥砂以俱行。年深日久, 河床因此日高。”[8]对于荒山崩山现象, 时人已经有较为深刻的认识, 意识到了正是由于森林荒废, 地面无所覆盖, 直接受风化作用, 表土容易随雨水而流失。民国二十年(1931年)《韩江水源林调查报告书》指出:“荒山崩山情形已如上述, 然山岭何由荒废?山岭何由崩坏?则其原因虽其复杂, 大概由于野火及滥伐之残害, 以致荒废。山岭荒废之后, 则地面无所被覆, 直接受风化作用。受风化作用之后, 则表土疏松, 随雨水而流失, 日积月累, 遂侵蚀而为野溪, 甚则地层陷落, 酿成山崩恶果, 欲图补救, 舍造林无他法也。”[9]对于森林保持水土的作用, 民国的雷文铨已经有了较为明确和科学的认识, 他在《查勘韩江水患报告书》中指出:“倾斜之地, 一遇雨降, 地面沙土, 常被流入河中, 壅塞河道, 而致水患。倘有林木蔓草, 则地下盘错之根茎, 可以增固土沙之团结力, 而抵抗流水之冲刷, 树上之树叶, 亦能减轻雨水下降冲击之力。至于地面树干草棘, 可以减少流水之速力, 因之而沙土不易流去。按流水速力与运送力之比较, 为六次乘方。例如速力增加一倍, 运送力则增加六十四倍矣。”[10]
二 对森林涵养水源作用的认识
森林是生态系统的核心, 具有多方面的环境保护作用, 不仅仅可以保持水土, 而且还有涵养水源的作用。康熙《埔阳志》中的《平沙村煽炉议》记载, 森林“斫伐大尽”的后果是:“冬则无以蓄水泉之源, 春则雪消雨涨, 山崩砂壅, 田地多致荒芜。”[3]康熙八年(1669年)的《官田王氏祠堂碑文》记载, 程乡县“承祖远下珠坊官田坑一派山林, 丛阴积泉, 以为灌荫, 粮田三十众石”, 后遭“兵民乘隙紊砍树木, 以致山光泉竭, 田地从此荒芜, 田课无得供输”。因此官府立碑示意:“坊官田坑一派灌阴粮田树木, 毋得任意采砍, 敢有故违, 许即指名示呈究, 决不轻恕须示。”[11]从碑刻记载中不难看出, 正是由于人们意识到了森林涵养水源的作用, 才告上官府, 请求立碑禁止“任意采砍”。乾隆《嘉应州志》也记载:“乃往者, 山中草木蓊翳, 雨渍根荄, 土脉滋润, 泉源淳蓄, 虽旱不竭。自樵采日繁, 草木根荄, 俱被划拨, 山土松浮, 骤雨倾洼, 众山浊流, 汹涌而出, 倾刻溪流泛溢, 冲溃堤工, 雨止即涸, 略旱而涓滴无存。故近山坑之田, 多被山水冲坏, 为河为沙碛至不可复垦, 其害甚巨。此宜培植草木, 以蓄养水源, 而后旱可不竭雨, 亦不致山水陡发也。”[12]其中, 对森林涵养水源的作用有了充分的认识, 并提出了“培植草木, 以蓄养水源”的建议。
清末民初, 随着近代西方科学知识与理论的不断传入, 人们对森林涵养水源的作用有了更为科学的认识。刘鉴仁对森林与水患之间关系已经有了深刻的认识, 他在《兴宁治水计划》中指出:“森林与水患关系密切之点, 一则根干盘互, 废叶腐积, 有固护土层及覆卫地面沙泥之益; 一则繁枝襛叶, 森干交柯, 有收过量水分及使雨水不至直射地面之益; 一则保存地润, 培地脉而荫泉源, 间接并有致雨防旱之益。”[5]时任潮州苗圃圃长的王显智在《整顿潮州苗圃计划书》中也指出:“森林能调和气候, 涵养水源, 丰富湿气, 固定砂土, 新鲜空气也。无森林之害, 水旱为灾, 洪水横流, 为中国十年来最大患害、最大问题。即吾潮韩江而论, 亦大灾数年一见, 小灾无年无之, 生命财产, 损失无穷。且水灾之后, 又往往继之以旱。嗟我居民, 逢此鞠凶。”[13]在分析了森林涵养水源作用后, 王显智感叹到:“然反观吾潮各属之林业则如何?童山濯濯, 遍地皆是, 点苍金碧, 千里荡然, 直接之木荒已见, 间接之水灾迭现”, 提出“苟欲除此苦海, 舍驾振兴森林之慈航莫由?”[13]民国时期一些有识之士在农林调查报告中也深刻分析了水患形成与森林破坏的关系。林纯煦等的《蕉岭县农业调查报告》记载:“至森林方面, 虽荒山甚少, 但成林者亦不多, 盖悉任天然之生长, 复随人意而砍伐, 此所以旱患叠呈也。”[14]丘实华等在《蕉岭农林现状调查》中也指出:“森林有调节气候, 捍止水旱之利, 尽人皆知。近年来县内之水旱灾迭起, 缺乏繁茂森林为之调节气候, 涵蓄水源, 实为主要之原因。考原有森林之被破坏, 实基于滥伐与焚烧, 故应对于现有森林, 弗论其为公私有, 尤与水源有密接关系者, 对于砍伐樵采, 均宜有相当之限制, 尤其关于烧山恶习, 更应禁绝及妥为预防之。”[15]雷文铨在《查勘韩江水患报告书》中更是深刻地指出韩江水患的根本原因在于森林遭到破坏, “全区地势倾斜, 地质多石, 兼乏森林, 致少有吸收雨量之能力”, “加之下游河道弯曲, 港汊分岐, 水势散漫, 河床渐淤, 排水日坏”。他进一步分析了森林在涵养水源方面的功能:“森林之于吸收雨量, 在地势多山倾斜之处, 益见其功效。盖无林木, 则雨水仅由地面迅速流过, 未受土沙吸收。若夫林木丛生之地, 则其树干及林中荆棘能阻滞流水, 且地上积叠枯叶蔓草, 有如海绵, 善于吸水。至于地中则因根茎盘错, 故土松而孔多。吸水尤易。据查森林之吸水量, 约及雨量全数百分之二十至三十五。由上种种流水, 因之而调匀, 可无流水急涨之患, 且不易干涸也。”[10]
三 对水患治理的认识及对策
水患灾害是生态恶化的综合表现之一。清至民国时期, 韩江流域水患灾害频繁, 对人们的生命财产构成了威胁, 影响了人们日常的交通运输, 甚至造成了社会秩序的不稳定。对于韩江流域水患的严重性和危害性, 时人已经有了较为深刻的认识。正如民国饶宗颐在《潮州志》中指出:“综观上述诸河之性, 中以韩江水患最为严重, 以其流域大而水量足, 远非其他各河所能比。”[16]韩江流域水患不仅严重, 而且危害大, 事关“民生之休戚”“文化之盛衰”。民国的朱宝岱在《造林刍议》指出:“潮梅, 处五岭之东, 重峰叠嶂, 地多沙石, 势又倾斜。韩江一流, 汇汀江、梅河诸水, 曲折纡回, 奔注其间。遇洪流则决堤, 漫野毁庐坏舍; 遇乾旱, 则交通阻塞, 灌溉艰难。水利不兴, 水患不除, 长斯以往, 潮梅大地不沦为泽国之区, 必变成贫瘠之域, 可不惧哉?况河流之叙畅梗阻, 关于民生之休戚, 人材之兴替, 文化之盛衰, 至为綦重, 韩江之病状若此。”[17]
面对水患灾害, 部分有识之士也针对性地提出了一些治理水患的对策。一是从治本着手, 提倡造林。提倡造林, 是人们对治理水患的一个根本性认识, 也是从根本上解决水患问题的一个办法。刘鉴仁在《兴宁治水计划》中详细阐述了治理兴宁水患的计划, 提出:“种山造林, 以护土而节流; 堵截崩冈, 以障泥而澄水, 所以治山实即所以治水; 而又于雨水出山之后, 入溪之前, 规复旧有塘堰, 以分盛涨而戢狂澜, 则源头清而根本治。”[5]潮州苗圃圃长王显智也认为:“夫根本治水之策, 非广植森林, 不能一劳永逸, 盖以森林能迂缓山水之洪流免河水暴涨, 又能障固山腹之泥沙, 使河身鲜壅, 此均历经无数科学家之经验所承认者也。”[13]民国时期曾任梅县女子师范学校校长萧蔚秋也认为:“韩江各地, 大都童山濯濯, 林地颓败已达极点, 影响所及, 山河崩俎, 水患频仍, 交通维艰, 是以有韩江治河处之设。然治河办法, 不过疏河固堤已耳。此等土木工事, 究非根本救济之法。欲图一劳永逸, 莫若造林。盖森林有涵养水源之作用, 改良河道之效。”[18]民国的陈秉元在《为浚韩江事告侨暹父老书》中提出“上游则奖励植树, 以保沙土”的办法, 然后“群策群力, 共成斯举”, 这样“不独交通利便, 商业繁盛, 而堤防坚固, 乐业安居”, 而且“是真我潮梅百世根本大计也”[19]。二是从治标着手, 疏浚河流。提倡造林, 从根本上治理水患, 固然是治本的良方, 然而对于已经出现的水患, 还需要治标, 疏浚河流。正如刘鉴仁所言, 治山办法, “以治普通水患固已行所无事”, 然“举治县属河身日高、水道大坏之河”, 则“病困虽发在山者, 病候已发在水”, 其“治标之法, 道在疏浚”。他认为: “兴宁沿岸水乡, 千数百顷计, 今日之低洼泽国, 皆当年之沃壤膏腴, 若将挑浚之沙泥, 实填河干之低地, 则耕地悉出, 而泥沙不忧。”[5]同时, 刘鉴仁还提出:如果真要实施疏浚之法, 还需要培养治水人才, 因为“凡全部之雨量、及平年之雨数、及沿岸地形、水流状况, 均需有精密之测量, 确实之计算”, 这些都需要水学专家才能做到。为此, 他提出了“要养成水学人材为亟”, 重视人才的培养, 建议县局设法派送数人到当时全国水利唯一学校— — —南京工程学校学习, 学成后再回来筹办治水[5]。清末丰顺的丁日昌在《复张寿荃观察论潮州水患书》也提出了“疏浚河流”的方法, “治河之策, 其说不一, 或浚支河, 以分其势”, 而“其尤要, 则疏浚河之尾闾, 将有碍水道沙田, 悉数开通, 曲者直之, 浅者深之”, 然后“溜势可以挟沙东趋, 旧沙能去, 则新沙不积”, 并“仿制黄河所用之滚江龙, 于上下游随时梳刷”, 才能达到“一劳永逸, 而吾潮可免城决堤溃之虞矣”的效果[20]。
二. 人们的森林生态保护
森林的大面积破坏, 导致了森林生态系统遭到严重的失衡, 由此引发了一系列的生态灾难, 给人们的生产和生活造成了严重的影响。地方官吏、士绅和乡民等采取了一些保护森林生态的措施, 主要从两个方面着手, 一从保护林木的角度出发, 订立乡规民约, 立碑护林, 制止人们的滥砍滥伐行为; 一从植树造林着手, 提倡和进行造林的实践, 从根本上解决森林大面积破坏的问题。
一 订立乡规民约, 保护林木
清至民国时期, 韩江流域的地方官吏、士绅和乡民通过订立乡规民约, 保护林木, 这主要体现在散落于乡村中的护林碑上。清至民国时期, 韩江流域的人们为了保护林木, 竖立了不少护林碑刻, 尤以清代为多。据倪根金对中国传统护林碑的研究, 明代为中国传统护林碑刻的发展期, 清代为中国传统护林碑刻的鼎盛期, 而到民国时期, 由于现代意义上的林业法规不断出现, 护林碑刻的空间开始受到挤压, 成为中国传统护林碑刻的转型期[21]。具体来说, 我们可以将林木的保护分为官方和民间两个层面。
1 官方护林
主要是指由地方官府为主导竖立的保护林木的禁碑, 禁止人们的乱砍滥伐。根据笔者所见, 现将这一时期韩江流域的护林碑列表如下, 由表 1可以看出, 这一时期的护林碑刻多由官方谕示。
表 1 清至民国时期韩江流域的护林碑
由表 1可知, 从清初至民国二十六年(1937年), 韩江流域共有官方示谕的护林碑17通, 其中清代就有13通, 占了大部分。就分布的空间而论, 以客家山区的梅州地区居多, 将近占总数的一半。地方官吏作为地方社会的领导者和管理者, 在具体的护林实践当中发挥着主导作用。首先, 颁立护林告示。大部分护林碑都是在地方官吏直接领导下颁立的, 颁立者多为七品县官。如现存潮州归湖镇西林学校的嘉庆二十三年(1818年)的“禁碑”就是当时的海阳县令竖立的; 又现存五华双华区军营乡的乾隆二十九年(1764年)的“廉明太爷丁奉道审详给风围水口碑”也是在村民的呼吁下, 由当时长乐县(今为五华县)县令所立的; 至今保存在大埔高陂中学的“奉宪严禁碑”为光绪八年(1882年)饶平县令卢蔚猷颁立。其次, 公正裁断毁林案。乾隆年间五华县的廉明太爷丁奉道, 是一位为官清正廉明的县令, 公正无私地审判了不法乡绅盗伐风围水口山上林木案。乾隆二十七年(1762年), 在长乐县出现了“盗卖荷村凹风围树木, 与奸商越境烧炭, 得银分肥”的毁林事件, 后经丁奉道“当堂查讯”, “谕断荷树凹树木俱系前朝人遵守, 以作通乡风围水口, 另有前任各官示禁, 无人敢伐”[22]。在他离任之后, 村民为了纪念他的护林功绩就立下此碑, 碑上面还刻有横批“廉明太爷丁奉道”。或许正是丁县令护林遗风尤存, 保护风水林在当地已经形成了一种传统。再次, 通力合作, 联防护林。地方官吏之间也加强协作, 共同保护林木。光绪八年(1882年)饶平县令卢蔚猷, 有感于山林辄遭乱砍滥伐, 饶平、大埔以及平和(福建省辖境)三县尤甚, 童山秃岭比比皆是, 分别致书大埔、平和二县, 略谓“山不禁则森林毁, 岭裸露则水土失, 栋梁枯则土木废, 薪炭尽则炊烟断”, 呼吁毗邻县治“为千秋山河, 万民生聚, 协力同心, 彼此环顾”。因之, 三县共商护林联防措施, 各派衙役乡勇巡视边界, 并各自制订内容相近的禁令告示, 其中大埔县勒石的告示犹存[23]。
此外, 在林木保护中还往往依靠生员、监生等地方乡绅的管理力量。不少保护林木的告示都是在他们的陈情和呼吁下颁布的。如乾隆二十九年(1764年)五华县, “据监生张开元, 子民张立安、赖声扬等具禀前事称”, “丰邑奸商邹聚锦于乾隆二十六年顶接丰顺县前山铁炉”, “越境取木烧炭”, “影占官山”[22]。同治八年(1869年)嘉应州阴那山, “现据教谕李闳中等赴辕呈称, 雁洋有阴那山、灵光寺……近因无知乡人在该庵焚烧水炭及藉名采取枯枝, 砍伐豆签, 实即盗采混砍, 以致山木日少, 泉源日竭”[24]。乾隆三十七年(1772年)大埔县, “据同仁双坑生员何其煌、何殷勤、何经国、何廷光、何弼良、何光华, 贡生何廷扬, 子民肖玉盛、何乃敬、丘士纶、陈东升、罗上拔, 保长谢宗玉呈称”, 当地官府“竖立石碑, 严禁盗斫焚山”, 如有人“借影盗斫, 放火焚烧, 一经巡山公人拿获, 许即指名禀赴本县, 以凭差拘严究”[25]。
2 民间护林
民间护林主要是依靠民间的力量, 通过制定乡规民约, 竖立禁碑告示, 对滥砍滥伐行为进行约束或者惩罚。在所见的乡村护林碑当中, 也有不少是“村民众议”[22]、“宗族公议”[22]或者是“村寨公议”[22]的。在这些主要依赖民间力量竖立的护林碑当中, 往往制定有村民达成一致的一些民间规约。对于盗偷林木者, 一般都要处以一定的惩罚, 或者罚钱, 抑或罚戏; 对于护林有功者, 则给予一定的赏钱, 以资鼓励。乾隆四十九年(1784年)平远县的《县奉主陈大老爷准示严禁碑》就规定:“禁盗偷山林竹木, 以及桐油子茶田禾种作等项者, 罚钱一千文, 捉获者赏钱三百文。禁盗挖竹笋并盗竹, 罚钱五百文, 捉获者赏钱三百文。”[22]对于祖宗遗下的成材林或是风水林, 一般都有明令禁山规约。如大埔县银江乡林区的田姓, 在清代就订有禁山的山规:“兹立山规, 维护山林, 禁区林木, 刀下留情。初犯罚戏一台, 效尤罚以重金。凡我上下林民, 护林务必同心。人人遵规守法, 代代繁衍昌盛。”[26]民国二十六年(1937年)《南澳县护林公约》对于盗伐者、护林者以及保护不力者都有详细的规定。对于“凡盗伐公有林”, 除“按价赔偿外, 仍须每株罚大洋五元”。“凡拔折苗木者, 每株罚大洋贰元, 犯者如属小童, 则罚其家长”。对于“举报作证者”, 则“以罚金半数奖给之”, 相反“诬告者反坐”。“县有林应由附近乡区保管, 如同时被盗伐十株以上, 不能发觉举报者, 应归该乡区公所负责。”[27]民国《兴宁林业会章程》中第15条至第18条为林规禁条, 其中也对盗伐、破坏林木行为有较为严格的惩罚规定。如“无论何项林木, 除荆棘散材外, 非至满尺以上, 不得斩伐, 违者查明处罚”, “除林业会指定为公众薪场外, 其前往私人林场樵采者, 仍应给回一定之薪价, 多少由各地林业会定之, 但樵采以蓾草为限, 若因樵采而斫伐林木者, 仍以盗伐论”, “有盗伐林木者, 与接受盗偷林木者, 轻者处罚, 重则送究, 至查明其人, 既非种户, 复未向人贩卖, 忽有木材出卖者, 以盗伐或窝论”[5]。
此外, 乡民还成立“禁山会” “看山会”等组织, 组成巡逻执罚的守青队, 切实履行禁山规约。据乾隆十七年(1752年)的大埔双坑《十八公引》记载: “厥后公举梅村兄、雨苍兄、乃及侄、乃敬侄与夫巡山诸人先后看理。”[25]这里的“巡山诸人”, 实际上就是负责巡逻的守青队。乾隆三十七年(1772年)大埔的《合乡禁山呈请温县主给示文》也记载:“仍设巡山一名, 不时稽查, 如遇盗斫焚山, 拿获赃贼, 指名禀报法剪。”[25]嘉庆《大埔县志》也有“近时城厢绅士, 复于城息租内岁抽三石, 给二人看守后山树木”的记载[28]。民国时期, 五华县的夏阜、华阁、近江、老楼、锡坑等乡村均有“禁山会”; 文葵五联乡则成立“看山会”, 专业管山员4人, 配枪巡山, 每人每年除领取生活补贴费外, 还发给一二斗谷作草鞋钱[29]。民国三十四年(1945年), 国民政府行政院重新公布修正《森林法》, 潮阳县各乡村也普遍订立乡规民约, 由守青队保护林木[30]。
二 提倡植树造林, 维护生态系统平衡
通过保护林木达到保护森林生态的目的, 这只是治标不治本的方法。要从根本上改善森林生态环境, 还需要提倡植树造林。有鉴于此, 清至民国时期韩江流域不少的地方官吏、有志之士还通过提倡和践行植树造林来维护森林生态系统的平衡。
清乾隆四年(1739年), 平远县的陈彰翼在项山植树造林, “捐俸栽松树叁千株, 上起城根, 下至进路两旁, 分列夹道, 酌筑护垣以拒畜牧”, 数年后“郁郁葱葱, 满城佳气, 士掇巍科, 民登毂车”[31]。民国时期, 在地方官吏、有志之士的大力倡导下, 开展了多种形式的植树造林运动, 既有政府造林, 也有民间造林, 其中以政府造林为主。政府造林, 主要是指以地方政府为主导力量的造林形式, 也可以称为“公营林业”。政府造林主要表现为以下几个方面:第一, 设立专门管理林业的机构。民国时期, 为了更好地植树造林, 设立了专门管理林业的机构。民国十九年(1930年), 潮阳县政府设建设科, 兼管林业。民国二十四年(1935年), 成立农业推广处, 民国三十八年(1949年), 并入第四科(建设科)[31]。民国二十一年(1932年), 兴宁县政府建设委员会成立林务组, 民国二十八年(1939年)三月改为建设科。同年, 广东省建设厅农林局在兴宁设立“东区林业促进指导区”, 管理粤东地区林业工作[32]。第二, 创办国营林场。国营林场是植树造林的重要场所, 也是政府造林的一种重要形式。“潮州之有官办林场, 始自清宣统二年, 未几, 因鼎革而罢。”[33]民国时期, 兴梅各县兴办有面积不大的国营林场。民国二十五年(1936年), 大埔县设立国营林场。至民国二十九年(1940年), 兴宁、五华、丰顺、蕉岭、大埔等县共设立国营林场11个, 面积1 833亩[34]。民国三十六年(1947年), 蕉岭县有林场5个, 均栽培油桐、桉、松、相思、合欢等[35]。第三, 培育苗圃。培育苗圃, 是造林的一个重要环节。民国十四年(1925年), “广东实司复于农事试验场旧址设潮州苗圃, 育苗百万株, 颇有成绩”。民国十八年(1929年), “省农林局林政营林二股, 以计划主理林业事项, 令各县遍设苗圃林场, 培育树苗, 提倡造林, 吾潮各县亦先后成立”。民国二十二年(1933年), “成立东区模范林场办事处于潮安县南校场, 同时设立东区苗圃三处林场及苗圃, 经常费由总部给, 而开办费由绥署发给”[33]。现根据民国《潮州志》的记载, 将民国二十六年(1937)潮州各县林场和苗木情况列于表 2。第四, 开展植树运动宣传。民国年间, 在韩江流域成立的潮梅总苗圃, 为韩江上游最高之林务机关。民国十九年(1930年), 在潮梅总苗圃的努力下, 由技术部提出植树运动宣传大纲, 通饬各县分圃遵行, 在各县属分圃开展了植树运动大会的宣传活动。经过植树宣传之后, 民众渐渐对植树造林的重要性有了更清醒的认识, 诚如罗振基等在《十九年度梅属各县植树运动大会之述评》的总结当中所言:“梅属各县人士, 在数年前之举行植树节, 仅以为循例之事, 关于植树之利益, 固无人负责推广, 即政府规定植树节之意义, 亦诸多不明白者。三年来赖总分各圃职员随时随地宣传, 民众始渐知山林荒废之危机而注意提倡植树。”[36]
表 2 民国二十六年(1937年)潮州各县造林情况
民间造林, 是指以民间私人力量为主体的造林形式, 或可称之为“私营林业”。除了政府倡导造林外, 大部分的植树造林都是由民间私人团体来完成。如兴宁县, “所属山多, 居民以林业为生活者殊众。年来复经政府之倡导, 造林事业, 日益发达。计自(民国, 编者加)十八年至今, 集资组织造林团体, 呈县备案保护者, 约有数十家。而私人经营, 规模较小者, 亦甚多”[32]。这种造林形式主要表现为以下两个方面。
第一, 有识之士兴办树木公司或垦殖场, 这是民间造林的一种重要形式。兴宁县就有不少有识之士兴办过一些树木公司或垦殖场。宣统三年(1911年)冬, 龙田人罗则恒以白石岭张庙塘祖尝山为基地, 集股兴办蓼塘罗族树木公司。在其影响下, 曲塘的学洒公树木公司、车沥的长岗埂树木公司亦相继建立。此后, 叶塘人萧惠长也于民国十五年(1926年)买得九莱口牛头坑、社坑里两坑田和山地近千亩, 成立务本实业公司, 雇工耕田育林, 经营10年, 民国二十五(1936年)转让给新陂李沽之经营。民国二十九年(1940年), 宁塘石子岭村商人李谷兰在金刚坑一带兴办辉生垦殖场, 营造水土保持林[37]。不仅兴宁出现这种造林形式, 潮阳、南澳等县也有类似的情况。民国二十八年(1939年), 潮阳著名旅暹侨领陈美堂回乡组建三民林业有限公司, 领耕田心华林一带荒山万余亩; 清末进士范家驹族人组成茂毓公司于和平牛踏埔耕山1 000余亩; 简朴乡民组成简朴造林公司领耕南山山地3 000余亩。各公司均营造马尾松、台湾相思林, 后因日军入侵而停业[30]。南澳县, 迩年邑人有补救弊之图, 计先后组织公司, 或用个人名义承垦官荒者, 凡十有五家。如益民益生等公司, 种有松柏等树数十万株, 今已枝叶挺秀, 蔚然成林[38]。
第二, 乡民承祖利用山地, 或在村宅旁或祖墓旁种树。这是另外一种民间造林的形式, 主要是乡民因迷信风水, 或为保墓而进行的自发造林。正如民国《潮州志》所言:“州境林业, 除少数专组公司经营外, 多系山间乡民承祖利用山地从事, 然数亦不多, 至农村宅旁或祖墓堤壩园囿零星树木, 则因乡民迷信风水, 或为保墓, 或抵水白, 或为抗风坳, 或为增添园囿风致而已。”[33]乡民之间也有合股经营种树。如辛亥革命后, 国民政府倡导造林, 潮阳县山村乡民多在私山垦荒种果或参股经营房头山[30]。又民国十六年(1927年), 兴宁新陂区石陂头的蓝水风、蓝金水倡议凑股种树, 3年内把仙人坐石周围300余亩祖山种上树, 持续经营至解放, 获益颇大。乡民也有在房前屋后种植经济林的, 如兴宁就有群众在房前屋后种植龙眼、桃、李等经济林的传统习惯[32]。
不管是政府造林, 抑或民间造林, 都有积极作用, 在某种程度上弥补了韩江流域森林破坏造成的损失。然而, 由于政局变动、战争频繁等种种原因, 植树造林运动的实际效果受到影响。就政府造林而言, “民国肇造, 政府虽常提倡造林, 然因战事频仍, 主其事者, 又执行不力, 朝设暮废, 时间既暂实施, 情形亦案卷难稽”[33]。以民间造林而论, “除少数附山乡村居民承祖遗, 有林业经营外(以大埔、丰顺及饶平三县最多), 专组公司领荒者虽不乏人, 然揆诸实际, 或因粮山为避免侵占, 呈请领荒以存主权, 或强族绅奢垂涎官地而报告垦殖, 故多有名无实。间或有志图此者, 又多因政府不切时实保护, 或为兵灾所摧毁, 或受人事所牵制, 驯致收益, 失望后继裹足”[33]。“至于公营林业, 则作辍靡, 恒无一贯之经营, 少认真之抚育, 往往徒具造林之名, 实成葬树之举, 尤为潮州林业不振之最大原因。”[33]
三. 结语
生态史是20世纪70年代以来史学界兴起的一个新的研究领域, 诚如英国著名的社会史学家彼得·伯克教授所说:“70年代以来, 在历史写作领域里, 有两个重大的变化, 一个是生态史的出现, 这里我不过多涉及; 另一个就是新文化史的出现, 或者称社会文化史, 它经常被视为更广泛意义上的文化转折。”[39]目前, 学术界关于生态史的研究, 多集中于生态的变迁以及变迁所造成的影响研究, 正如王子今先生所言:“生态史学主要包括两个方面的内容, 其一即生态条件本身历史的研究, 其二则是生态条件对社会历史之影响的研究。”[40]然实际上, 作为生态系统中的重要组成部分之一的人类, 面对因生态系统破坏而造成的对自身生产、生活的影响, 不管在思想意识层面抑或行动层面都会做出自然的应对。
可以说, 正是因为清代至民国时期韩江流域出现了严重的水土流失、江河淤塞及水患灾害频仍等问题, 才引起了当地地方官吏、士绅以及有志之士对韩江流域森林生态问题的广泛关注, 并开始逐渐反思保护林木与水患灾害的关系, 提出了不少真知灼见。这些关于森林涵养水源、保持水土流失以及水患灾害关系的认识, 是人们在生态灾害面前做出的正确判断, 也是人们生态保护意识逐渐觉醒的表现。在思想意识的影响下, 人们在行动上做出了应对, 通过采取订立乡规民约、竖立护林碑、提倡和践行植树造林等措施保护森林生态系统。毫无疑问, 当时人们的生态保护意识和行动, 保护了韩江流域的生态, 有效地遏制了韩江流域进一步的生态恶化, 也为我们今天的生态意识和实践的形成做出铺垫, 实在功不可没。尽管由于时代政局的不稳, 清至民国时期人们的生态保护行为缺乏系统性, 也没有制度保障, 但当时韩江流域有志之士大力倡导植树造林运动, 对我们今天的生态文明建设和生态环境的保护仍然具有重要的借鉴意义。
-
表 1 清至民国时期韩江流域的护林碑

表 2 民国二十六年(1937年)潮州各县造林情况

-
[1] 吴建新.明清广东山区的宗族与山林保护: 以大埔县《崧里何氏族史(七修)》为中心[G]//倪根金.梁家勉先生诞辰100周年纪念文集.北京: 中国农业出版社, 2010. [2] 关传友.论中国古代对森林保持水土作用的认识与实践[J].中国水土保持科学, 2004(1):105-106. doi: 10.3969/j.issn.1672-3007.2004.01.022 [3] 宋嗣京.埔阳志: 卷1[M]//中国地方志集成: 广东府县志: 辑21.上海: 上海书店出版社, 2003: 316-434. [4] 蔺绣.大埔县志: 卷1[M]//广东历代方志集成.广州: 岭南美术出版社, 2009: 536. [5] 刘鉴仁.兴宁治水计划[M] //罗香林.兴宁先贤丛书: 第10册.香港: 兴宁先贤丛书校印处, 1977: 3-24. [6] 王延康.筹浚潮州韩江刍议[M] //韩江治河处.韩江治河处第一期报告表.广州: 广东省立中山图书馆, 1925: 1. [7] 林纯煦, 何庆功.兴宁县农业调查报告[M] //国立中山大学农学院.广东农业概况调查报告书续编: 上卷.广州: 义昌印务局, 1929: 75-76. [8] 谢雪影.潮梅现象[M].汕头:时事通讯社, 1935:80. [9] 李觉, 许纬东.韩江水源林调查报告书[M].广州:广东建设厅农林局, 1931:18. [10] 雷文铨.查勘韩江水患报告书[M].汕头:韩江治河处, 1922. [11] 周建新.民间文化与乡土社会:粤东梅县五大墟镇考察研究[M].广州:花城出版社, 2002:204-205. [12] 王之正.嘉应州志:卷1[M].广州:广东省中山图书馆古籍部, 1991:38. [13] 王显智.整顿潮州苗圃计划书[M].潮州:潮州苗圃, 1926. [14] 林纯煦, 何庆功.蕉岭县农业调查报告[M] //国立中山大学农学院.广东农业概况调查报告书续编: 上卷.广州: 义昌印务局, 1929: 53. [15] 丘实华, 黄廷昌, 徐彦.蕉岭农林现状调查[M] //广东东区农林讲习所.东区农林.潮州: 永昌印务局, 1933: 19. [16] 饶宗颐.潮州志·水文志[M].汕头:潮州修志馆, 1949. [17] 朱宝岱.造林刍议[M] //韩江治河处.韩江治河处第一期报告表.广州: 广东省立中山图书馆, 1925: 15. [18] 萧蔚秋.韩江周岸造林的我见[M] //潮安林场.山林.广州: 广东建设厅农业局潮安林场, 1931. [19] 陈秉元.为浚韩江事告侨暹父老书[M] //韩江治河处.韩江治河处第一期报告表.广州: 广东省立中山图书馆, 1925: 5. [20] 饶玉成.皇朝经世文编续集: 卷119[M] //沈云龙.近代中国史料丛刊: 第85辑.台北: 文海出版社, 1972: 6332-6333. [21] 倪根金.中国传统护林碑刻的演进及在环境史研究上的价值[J].农业考古, 2006(4):225-229. doi: 10.3969/j.issn.1006-2335.2006.04.034 [22] 谭棣华, 曹腾腓, 冼剑民.广东碑刻集[M].广州:广东高等教育出版社, 2001:336-906. [23] 广东省林业志编纂委员会编辑室.广东林业大事记(304— 1987)[M].广州:广东省林业厅, 1994:4. [24] 李阆中.阴那山志[M].程志远, 增订.广州: 广东旅游出版社, 1994: 330. [25] 崧里何氏族史修编工作委员会.崧里何氏族史[M].大埔:崧里何氏族史修编工作委员会, 1996:1189-1191. [26] 黄玉钊.梅州客家风俗[M].广州:暨南大学出版社, 1992:14-15. [27] 汕头市林业志编纂委员会.汕头市林业志[M].汕头:汕头市林业局, 1990:174. [28] 洪先焘.大埔县志: 卷2: 山川志[M] //广东省立中山图书馆藏稀见方志丛刊: 第37-38册.北京: 国家图书馆出版社, 2011. [29] 五华县志编纂委员会.五华县志[M].广州:广东人民出版社出版, 1991:142. [30] 潮阳市地方志编纂委员会.潮阳县志[M].广州:广东人民出版社出版, 1997:293. [31] 卢兆鳌.平远县志: 卷1[M] //中国地方志集成: 广东府县志辑21.上海: 上海书店出版社, 2003: 19. [32] 兴宁县志编纂委员会.兴宁县志[M].广州:广东人民出版社, 1992:221-222. [33] 饶宗颐.潮州志:实业志2:林业经营[M].汕头:潮州修志馆, 1949. [34] 梅州市志编纂委员会.梅州市志[M].广州:广东人民出版社出版, 1999:800. [35] 蕉岭县地方志编纂委员会.蕉岭县志[M].广州:广东人民出版社出版, 1992:196. [36] 罗振基, 傅思杰.十九年度梅属各县植树运动大会之述评[J].农声, 1930(133):41-58. [37] 广东省民政厅.广东全省地方纪要:第33编:兴宁县[M].广州:广东省政府民政厅, 1934:58. [38] 广东省民政厅.广东全省地方纪要:第61编:南澳县[M].广州:广东省政府民政厅, 1934:313. [39] 杨豫, 李霞, 舒小昀.新文化史学的兴起:与剑桥大学彼得·伯克教授座谈侧记[J].史学理论研究, 2000 (1):143-144. doi: 10.3969/j.issn.1004-0013.2000.01.018 [40] 王子今.中国生态史学的进步及其意义:以秦汉生态史研究为中心的考察[J].历史研究, 2003(1):107. http://www.cqvip.com/qk/81900X/200301/8904776.html -
期刊类型引用(3)
1. 衷海燕,蔡文溢. 民国时期韩江的治理与大型水利工程的兴修. 韩山师范学院学报. 2020(04): 43-50 .  百度学术
百度学术
2. 张文琴. 改革开放四十年来中国近代林业研究综述. 农业考古. 2020(03): 257-264 .  百度学术
百度学术
3. 李盼杰. 生态文明建设的辩证法探究——以福建省生态文明建设实践为例. 厦门广播电视大学学报. 2019(03): 67-76 .  百度学术
百度学术
其他类型引用(1)
计量
- 文章访问数: 1187
- HTML全文浏览量: 242
- PDF下载量: 189
- 被引次数: 4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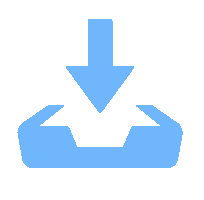 下载:
下载: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