Multi-disciplinary Paradigms of "Ecology+" Research in the Field of Humanities and Social Sciences
-
摘要:
人类曾过度关注和追求自身利润的最大化,忽视了自然规律,导致了人与自然关系的紧张,出现了生态系统退化、环境污染、生物多样性缺失等生态环境危机。进入21世纪,人类越来越意识到,要树立新的生存理念,尊重自然、顺应自然、保护自然,才能实现可持续发展,因此,“生态”研究引起了社会各界的关注,成为研究和热议的主题之一。通过广泛研究,论文分析了人文社会科学领域中“生态 + 社会思想”“生态 + 文学”“生态 + 语言学”和“生态 + 翻译”四个重要学科交叉融合的研究范式,以期为读者提供一个“生态+”研究的宏观图谱,彰显人文社会科学对社会发展和生态保护的高度关切,也为应对生态挑战提供多方位、多层次的思考维度。
Abstract:Humans once paid too much attention to and pursued the maximization of their own profits, ignoring the laws of nature, which led to the tension between man and nature, and the ecological environment crises of ecosystem degradation, environmental pollution and lack of biodiversity appeared. In the new century, humans are increasingly aware that only by establishing a new concept of survival, respecting, conforming to and protecting nature can sustainable development be achieved. Therefore, the study of "ecology" has attracted the attention of all sectors of society and become one of the hot topics of research and discussion. Through extensive research, this paper analyzes the research paradigms of the four important disciplines of "ecology + social thought", "ecology + literature", "ecology + linguistics", and "ecology+translation" in the field of humanities and social sciences, with the aim of providing readers with a macro-map of "ecological+" research, highlighting the concerns of the scholars of the humanities and social sciences for social development and ecological protection, and also providing multi-dimensional and multi-level insights for addressing the eco-challenges.
-
Keywords:
- ecology /
- social thought /
- literature /
- linguistics /
- translation
-
“生态”研究是近年来各个领域的热点词汇,引起了社会各界的关注,成为研究和热议的主题之一。“生态”研究的兴起有其必然的时代背景、社会根源和发展历程。自然为人类生存提供了必要的条件,人类在与自然的互动中,得到了自然的馈赠。但人类只关注和追求自身的利益最大化,无视自然规律,无限扩张,导致了人与自然的关系紧张,出现了生态环境危机,如生态系统退化、环境污染、资源趋紧、生物多样性缺失等问题。进入21世纪以来,人类越来越意识到,要树立新的生存理念,即尊重自然、顺应自然、保护自然,取之以时,取之有度,天、地、人和谐统一,才能实现可持续发展。
“生态学自获得发展以来,似乎就已经因其对生命本身的关注而担负起了重要而广泛的使命,以至于它在多个学科领域都成为了被参照、借用、嫁接的思想和理论范式,并催生和拓展了新的研究视域。”[1]诚然,交叉融合是学术研究和创新活力的重要源泉之一。自然科学的生态研究主要关注众多生物有机体之间、生物有机体与外界环境之间的相互影响、相互关系与作用;人文社会科学的生态研究则更加关注人类与自然环境的相互关系及社会变革的方向,探讨人类社会思想、制度、文化、价值观和行为对生态环境的影响。通过广泛研究,笔者分析了人文社会科学领域中“生态+”四个重要学科的交叉融合研究及其范式,以期为读者提供一个“生态+”研究的宏观图谱。人类社会发展中出现的复杂问题、存在的差异与冲突,从人文社会科学的研究与视角出发,可以为其提供多方位、多层次的思考维度。
一. 生态 + 社会思想——生态文明
任何先进的思想都不是一蹴而就的,而是有其必然发展的过程。人类文明经历了原始文明、农业文明、工业文明之后,目前所处的生态文明是一种崭新的、高级的新型文明形态,是人类社会发展到一定阶段的必然产物。超越工业文明,即要超越工业文明时期的一些过度以自我为中心的价值理念,诸如征服自然和人类中心主义,取而代之的是要思考如何与自然平等相处、和谐共生,如何对后工业文明衍生的生产生活方式及其制度进行生态化改造和绿色转型。人与自然、人与社会、人与自身关系在工业革命后,需要思考如何重构重塑价值体系,兼顾整体性、综合性和协调性,其中包括人文环境与自然环境、思想与制度、社会正义与环境公平。
早在2007年,党的十七大报告提出,要建设生态文明,基本形成节约能源资源和保护生态环境的产业结构、增长方式和消费模式[2]。2012年,党的十八大报告第八部分详述了这个重要的战略决策,即“大力推进生态文明建设”,指出要将生态文明放在突出地位,明确了生态文明建设要融入经济建设、政治建设、文化建设、社会建设各方面和全过程,形成建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五位一体”的总布局,努力建设美丽中国,实现中华民族永续发展[3]。十八大报告为我国生态文明建设擘画了宏伟蓝图,其重要意义关乎人民的福祉、民族的未来。2017年,党的十九大报告指出:坚持人与自然和谐共生,树立和践行“绿水青山就是金山银山”的理念,坚持节约资源和保护环境的基本国策,建设生态文明是中华民族永续发展的千年大计;我们要像对待生命一样对待生态环境,统筹“山水林田湖草”系统治理,实行最严格的生态环境保护制度,建设美丽中国,为全球生态安全做出贡献[4]。2018年5月,习近平总书记在全国生态环境保护大会上强调,要通过加快构建生态文明体系,自觉把经济社会发展同生态文明建设统筹起来,加大力度推进生态文明建设、解决生态环境问题,坚决打好污染防治攻坚战,推动我国生态文明建设迈上新台阶,确保到2035年,生态环境质量实现根本好转,美丽中国目标基本实现[5]。2021年4月,习近平总书记在领导人气候峰会上,向世界阐释了“共同构建人与自然生命共同体”的理念,揭示了对人与自然生命共同体的规律性认识,指出要大力加强生态文明建设,谋求人与自然和谐共生之道的新格局[6]。2022年,党的二十大报告再次明确阐述了生态文明建设的重大意义。自然是人类赖以生存发展的基本条件,是全面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国家的内在要求。生态文明建设是中国共产党为人民谋幸福、为民族谋复兴、为世界谋大同的新方向与新作为。中国式现代化是“绿色”“可持续发展”的现代化,是将生态文明建设融入到全局发展中的现代化[7] 。
生态文明思想继承了人类文明思想的精华,关注人类的整体发展,又尊重区域性差异,传递了中国生态智慧,是继承性和创造性的有机统一。“生态文明是具有新的文明要素的更高级文明形态,生态文明的本质是人与自然和谐共生,生态文明是与社会主义社会相适应的新文明”[8]。生态文明引起了社会各界的广泛关注,研究十分活跃,并取得了丰硕的研究成果。以“生态文明”为主题词,时间区段设定为从党的十七大报告首次提出建设生态文明到现在,即2007年1月1日—2023年1月1日,在“中国知网”上进行高级检索,可以看到与之相关的文献数量为135 863条;自2013年以来,与“生态文明”相关的研究文献每年的发表数量都在10 000篇以上。
二. 生态 + 文学——一种新的文学研究与批评范式
文学中的生态研究受启于生态学,其起源可以追溯到20世纪70年代初,美国学者约瑟夫·W.米克在他的著作The Comedy of Survival: Studies in Literary Ecology (《生存的喜剧:文学生态学研究》)中首次提出了术语“literary ecology”(文学生态学),并对出现在文学作品中的生物主题进行了研究。其后,另一位美国学者威廉·鲁克特在其论文Literature and Ecology: An Experiment in Ecocriticism (《文学与生态学:生态批评的实验》)中首先使用了“ecocriticism”(生态批评),把生态学以及和生态学有关的概念运用到了文学研究中[9]。由此,生态与文学相结合,生态被正式引入文学研究领域中。
将生态学引入文学研究领域,主要是对文学与其所处的社会环境间的关系进行研究,是对文学研究范式和领域的一次新的拓展。尹雪梅等[10]指出:西方在人本主义主导下,传统文学以人为中心,将自然排除在人的道德关怀范围之外,导致了传统文学与自然生命伦理的截然对立。生态文学对作家和作品从生态思想角度进行重新审读与评价,为当代西方文学批评提供了一个自然生态的新纬度,这是一种新型的文学批评范式。
20世纪80年代以后,文学的生态学研究在国内外不断获得重视,形成了多视角、多层次的文艺理论和文学研究范式,即生态批评、生态审美、生态文艺学、文学生态学等多种研究范式。国外出现了一批知名学者与重要作品,如弗雷德里克·O.沃格的《教授环境文学》、劳伦斯·布伊尔的《重评美国田园作品的意识形态》、彻丽尔·伯吉斯·格罗特菲尔蒂的《走向生态文学批评》、格伦·A.《实用生态批评:文学、生物学及环境》等。同时,国内学者也积极推进文学的生态研究,构建中国生态文艺理论,推进了中国生态文艺思想的发展,如鲁枢元的《生态文艺学》、曾繁仁的《生态美学导论》、徐恒醉的《生态美学》、袁鼎生的《生态艺术哲学》、曾永成的《文艺的绿色之思:文艺生态学引论》等,这些学者在文学生态研究领域作出了重要的贡献[1] 。
文学生态研究发展成一种新的文学研究与批评的范式,尤其是近几年随着时代的呼唤,发展势头更加强劲。文学研究者表现出了拯救地球生态环境的使命感和责任心,他们把关怀自然作为自己的神圣使命,摒弃了人类中心主义,迫使人类从傲慢的主宰地位退位,俯身成为大地共同体中平等的一员。他们将研究视域转为人类与生态系统中诸因素之间的关系,聚焦自然,关注受到人为破坏的环境,关注自然与社会文化的交叉与互动,是一种对人本主义批评和科学主义批评的历史性超越,旨在建立一种更为和谐的人与自身、人与他人、人与社会、人与自然的新型关系,达到了人与自然生态的新纬度。对传统文学重审和重评,是生态批评的一个主要任务。重审的直接目的是对反生态文学作品作出价值判断,从而推动学界对文学发展史作出整体性的重新评价和重新建构,推动人们建立起生态的文学理念[10]。
聚焦国内,众多学者在西方文学生态批评的影响下,积极融入了研究的潮流中,他们一方面对西方的生态批评展开辩证的研究与理论的运用,另一方面在研究中逐渐形成具有中国特色的生态批评思想,并在中西研究比较借鉴中拓展延伸了生态批评的研究视阈。在中国知网以“文学生态批评”为主题进行检索,可以看到在学术期刊上发表的论文有895条,博士论文有40条。中国学者的文学生态批评研究极大地丰富了生态批评研究的内容和思想,为西方提供了独特的中国视角,彰显了中国的学术力量和贡献。
然而,国内文学生态学研究尚处于起步阶段,其研究在理论和方法上的建构仍不够完善,并存在着一些问题。第一,一些研究的文学生态概念过于强调作品的自然属性,从而导致对非人类中心主义的盲目膜拜;还有一些研究者缺乏足够的文学生态学积累,生硬照搬生态概念和理论,将生态批评随意泛化;有的文学生态学研究停留在对作家、作品思想主题的解释上,还缺乏对生态文本的审美、语言等层面的研究[11]。第二,文学生态学研究领域也亟待新的界定和拓展。值得学者们思考,并且已经成为制约文学生态学发展的突出问题是:文学生态从自然、社会到文学自身的诸多构成因素,应该以一种什么样的结构呈现出来,它们各自在这一结构中应处于什么样的位置,它们应如何形成相互间的关联和作用,文学生态学研究如何确立自身地位并与其他学科领域相区别,从而使文学生态学之所以成为文学生态学[1]。
三. 生态 + 语言学——三种新兴交叉的研究范式
全球生态环境的日渐恶化引起了越来越多人对生态的关注与思考。生态研究涵盖了生物与自然界、人与人之间各种因素的互相依存关系的研究。由此,生态研究的理念、范围和范式逐渐从自然科学外扩与渗透到人文社会科学。语言学研究受到其影响,跳出了研究语言的框架或研究语言内部关系的结构主义园囿与藩篱,跨越了句法学、语义学、语用学等传统研究的范畴,形成了研究语言与环境互动关系的生态学和语言学相结合的新兴交叉学科——生态语言学(eco-linguistics)或语言生态学(ecology of language),对语言、思维与环境之间相互作用的关系进行研究,聚焦语言生存和发展的生态环境,“研究人类语言的生态性质,探究语言的生态伦理,揭示语言发展的生态规律”[12],即语言回归到了生态系统中,对其进行重新认识与研究。语言学与生态学的学科交叉,形成了如下跨学科的重要研究领域:语言的多样性、语言多样性导致文化多样性的相互关系、濒危语言的生存状况、语言系统中的生态和非生态因素、生态批评话语分析。跨学科领域的研究产生了两种截然不同的研究范式:一是运用生态学的方法分析语言系统,研究和解读语言系统和语言使用的非生态特征;另一种是研究分析语言生存与发展的生态环境,评估评价各种语言的生存状况[13]。
研究语言在解决生态环境问题中的影响和作用,促进语言和环境之间关系的和谐发展,西方最为知名的语言生态学研究范式是豪根范式、韩礼德范式和认知范式。豪根于1972年创新地提出了“生态隐喻”范式,将生态作为环境中“语言的隐喻”,探究各种增强或削弱语言功能的环境因素,即社会环境对语言的作用。豪根指出,良好的生态环境是语言进化、发展及保护的基本保障,而语言的生态平衡又影响决定着社会文化的生态平衡。韩礼德范式是指韩礼德在20世纪90年代提出的“生态批评语言学”范式,其包含两个分支:语言生态学和生态语言学(又称生态批评语言学),研究语言对生态环境的影响和作用。前者主要关注语言多样性、濒危语言、语言活力、语言政策、语言进化等问题,后者则更加关注语言系统的生态学分析、环境语篇的分析批评、语言对生态环境的作用、生态语法等领域的研究[14]。
对于上述两种语言学与生态学相结合的研究范式,目前国际上更多采用的是韩礼德范式的生态语言学或生态批评语言学;与此不同,国内生态语言学的研究,豪根范式却更受欢迎,国内学者采用此范式来探讨语言的文化生态环境,强调语言的生态保护。然而,国内研究还存在着不足,“缺乏对语言,尤其是汉语的生态话语批评或从生态角度对汉语语言系统的微观研究,期待今后的研究有所突破”[14]。
认知范式是由斯提比于2015年提出的,他借鉴了认知语言学的“概念隐喻理论”和“认知框架理论”来分析和阐释生态文本,构建生态话语,强调话语研究要进行生态分析,建构生态系统中的生态话语。认知范式中强调分析和建构话语是因为人们通过语言对自然的认知进行了概念化处理,这些概念又反过来影响着人们的言语,强化、弱化或改变着人们对自然的认知,指导、影响、控制着人们的行为[13]。认知范式的理论是基于认知语言学、生物生态共存观,研究方法是语篇分析法、批评话语分析法、认知事件分析法[15]。
四. 生态 + 翻译——中西同名异质的研究范式
生态与翻译研究的结缘,出现在21世纪初期。2001年10月,中国学者胡庚申为香港浸会大学师生讲授了自己的翻译研究“从达尔文的适应与选择原理到翻译学研究”,他把达尔文进化论中重要的术语和原理,如“适应/选择”学说、“自然选择”“适者生存”等引入了翻译研究中,由此开启了中国生态翻译研究的新范式。其后,他在国际译联第三届亚洲翻译家论坛上宣读了论文《翻译适应选择论初探》,为中国学者在生态翻译领域的研究奠定了基础。2004年,胡庚申撰写出版了首部专著《翻译适应选择论》[16],对自己在生态翻译领域的研究进行了系统的论述。他认为翻译和生物界是关联和通融的,翻译过程中译者不断“适应”和优化“选择”,翻译过程是一种“适应”“选择”“生存”“淘汰”的思维过程,是不断地排斥“差的”,保留“好的”,即“汰弱留强”。
生态翻译在中国本土诞生,是由胡庚申提出的原创性术语,“在当今的多学科交叉和新文科建设的大语境下,生态翻译甚至可以被当作一种人文学术研究的范式,对其他相关学科的建立并跻身国际学界起到某种引领和示范的作用”[17]。
胡庚申提出生态翻译研究新范式后,引起了国内翻译界的关注,对这一研究范式,有些基本概念和范畴还不够清晰。2008年,胡庚申进一步论述和阐释了生态翻译理论中一些重要概念的基础与研究范畴。生态翻译的基础是翻译生态和自然生态具有同构隐喻。生态翻译以生态的“适应/选择”理论为基石,系统探讨了翻译生态、文本生态和“翻译群落”生态及其相互关系和相互作用。生态翻译以东方生态智慧为依归,将基于整体主义的生态学与翻译学相结合,指导译者关注翻译生态系统的整体性。生态翻译学的出现标志着译学理论由单一学科转向跨学科视野和范式,其本质特点是多学科交叉的跨学科研究,是一种生态学途径的翻译研究范式[18]。
此后,胡庚申继续深耕生态翻译,不断发表论文和专著[19-24],对生态翻译研究的基本内涵、产生背景、发展基础、研究焦点、研究成果、现有研究的局限与不足,以及未来研究的发展空间等问题进行了更加全面深入的阐述。
在翻译理论方面,西方理论研究成果众多,西方学者一直处于“领跑者”的地位,中国学者基本扮演的是“追随者”和“实践者”的角色。然而,胡庚申提出的生态翻译研究范式,改变了翻译研究领域的现状,中国翻译理论研究跳出了“照着说”“接着说”的模式,开创了中国翻译理论“领着说”的先河[25]。
生态翻译研究在国外一直处于沉寂之中,鲜见系统论述,直到2017年,第一部生态翻译专著Eco-translation: Translation and Ecology in the Age of the Anthropocene[26](《生态翻译:人类世时代的翻译与生态学》,简称《生态翻译》)由全球著名的劳特利奇学术出版社出版。《生态翻译》以诸多新术语、新概念,拓展了读者的思维疆域,其中最重要的两个新术语是“anthropocene”和“tradosphere”。作者克罗宁指出,在anthropocene,即人类世时代,道德责任更为重大,只有把翻译实践定位于生态符号学的不同领域,这些领域构成一个可理解的世界,这种问责制才能开始运作。在书中,tradosphere的意思是信息在生物体和非生物体之间循环并被翻译成一种语言或代码,供接收实体处理或理解的所有方式,即地球上所有翻译系统的总和。作者提出tradosphere概念,希望向译者传达两方面的信息:一方面,纵观历史,人类与非人类彼此相互联系,没有非人类,人类是不可想象的,这种联系是建立在翻译实践基础上的。另一方面,像生物圈一样,tradosphere处于进化状态中,其在生态危机时期容易受到各种风险的影响,甚至可能威胁到其生存。译者在与“他者”的沟通中,要试图理解有机体或非感性物体所表达的意义,不是拟人化的主观推测,而是要客观地与不同的生物进行沟通,即翻译的实践和操作可能是不同物种之间的交流,翻译的内容是符际翻译,其研究对象不再局限于人类的语言。由此可以看出,《生态翻译》打破了传统关于翻译内容和研究对象的固有思维定式,拓展了翻译学领域相关问题的理解边界,开阔了翻译领域的研究视野,将翻译研究引入了超越人类学的生物符号学领域[27]。
中西生态翻译研究比较而言,学术名称似乎相同,然而其研究实质在内容、范畴、方法、思维路径上却大相径庭,彼此的研究范式显示了东方的系统与具体、西方的宏观与抽象。胡庚申教授的研究范畴是整个翻译生态系统,是一种生态学途径的2.0复合型跨学科、多学科交叉的翻译研究范式。从生态视角出发,依据“适应/选择”理论,他系统地研究了翻译生态、文本生态和“翻译群落”生态,认为翻译的过程是一种“适应”“选择”“生存”“淘汰”,是“汰弱留强”的过程。而克罗宁的生态翻译研究认为,译者要应对人类所导致的环境变化带来的各种挑战,翻译的对象范畴不再局限于人类的语言,而是人类/非人类之间的语言和符号,以期理解有机体或非感性物体的诉求,本质上是人类与不同的生物体进行沟通和交流。
五. 结 语
竭泽而渔,明年无鱼;焚薮而田,明年无兽。进入21世纪以来,随着人文社会科学对“生态”的关注,“生态”被推到了前台,成为各学术领域研究的热点。生态学和人文社会科学各学科“联姻”,学科交叉研究快速发展,有其必然的学科和社会背景。生态学研究的领域及内容相当广泛,不仅是对生态生物系统内部成分之间及其与自然界之间相互关系的研究,同时还是对人类社会人与人之间及其与所处的社会各因素之间相互关系的研究。
随着工业化进程的加快,现代科技高速发展,人类享受着更加美好的物质生活的同时,全球生态环境却不断恶化,生态问题越来越多地引起了世界各国学者的关注。生态学研究生物及其环境之间的相互关系,其科学理论渗透至不同的学科,研究范围也从自然科学拓展至人文社会科学领域,形成了生态科学和多门学科相结合的研究,即“生态+”多门学科的交叉研究范式,产生了丰硕的研究成果。“生态+”多学科研究范式,彰显了人文社会科学对社会发展和生态保护的高度关切。人文社会科学的研究以更加多维的视角来看待世界,有助于解决复杂问题,以构建和实现更加美好的未来。
-
[1] 荀利波. 文学生态学研究:基于学术史梳理的讨论[J]. 文艺评论,2017(12):66-76. [2] 胡锦涛在中国共产党第十七次全国代表大会上的报告(全文)[EB/OL]. (2007-10-25) [2022-06-11]. http://cpc.people.com.cn/GB/104019/104101/6429414.html. [3] 胡锦涛在中国共产党第十八次全国代表大会上的报告(全文)[EB/OL]. (2012-11-18) [2022-06-11]. http://politics.people.com.cn/n/2012/1118/c1001-19612670-2.html. [4] 习近平在中国共产党第十九次全国代表大会上的报告[EB/OL]. (2017-10-28) [2022-06-11]. http://cpc.people.com.cn/n1/2017/1028/c64094-29613660.html. [5] 习近平出席全国生态环境保护大会并发表重要讲话[EB/OL]. (2018-05-19)[2022-06-11]. http://www.gov.cn/xinwen/2018-05/19/content_5292116.html. [6] 习近平:共同构建人与自然生命共同体[EB/OL]. (2021-04-23) [2023-02-01]. http://www.xinhuanet.com/mrdx/2021-04/23/c_139901359.htm. [7] 许勤华. 读解二十大报告:中国生态文明建设为人民谋幸福,为世界谋发展[EB/OL]. (2022-10-26) [2023-02-01]. http://www.china.com.cn/opinion2020/2022-10/26/content_78485962.shtml. [8] 刘涵. 习近平生态文明思想研究[D]. 长沙:湖南师范大学,2019:Ⅱ. [9] 朱新福. 美国生态文学批评述略[J]. 当代外国文学,2003(1):135-140. [10] 尹雪梅,廖才高. 生态文学:西方批判文学的新范式[J]. 求索,2008(6):184-186. [11] 龙其林. 非人类中心膜拜、生态批评泛化及思想主题癖:对当前国内生态文学研究中常见问题的批评[J]. 青海社会科学,2018(40):159-184. [12] 黄知常,舒解生. 生态语言学:语言学研究的新视角[J]. 南华大学学报 ( 社会科学版),2004(2):68-72. [13] 王宏军. 论生态语言学的研究范式[J]. 外国语文,2019(4):84-89. [14] 段李敏. 生态语言学的渊源及研究范式[J]. 跨语言文化研究(第9辑),2016(1):92-100. [15] 马俊杰. 生态语言学研究中的“认知范式”[J]. 外国语言文学,2018(5):472-481. [16] 胡庚申. 翻译适应选择论[M]. 武汉:湖北教育出版社,2004. [17] 王宁. 生态翻译学:一种人文学术研究范式的兴起[J]. 外语教学,2021(6):7-11. [18] 胡庚申. 生态翻译学解读[J]. 中国翻译,2008(6):11-15. [19] 胡庚申. 生态翻译学:产生的背景与研究基础[J]. 外语研究,2010(4):62-67. [20] 胡庚申. 生态翻译学研究的焦点与理论视角[J]. 中国翻译,2011(2):5-9. [21] 胡庚申. 生态翻译学:建构与诠释[M]. 北京:商务印书馆,2013. [22] 胡庚申. 若干生态翻译学视角的应用翻译研究[J]. 上海翻译,2017(5):1-5. [23] 胡庚申. 翻译研究“生态范式”的理论建构[J]. 中国翻译,2019(4):24-33. [24] 胡庚申,罗迪江. 生态翻译学话语体系构建的问题意识与理论自觉[J]. 上海翻译,2021(5):11-16. [25] 武立红. 生态翻译学“领着说”的脉动线路图[C]//吴江梅,鞠方安,彭工. 现代外语教学与研究(2019). 北京: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19:325-331. [26] CRONIN M. Eco-translation:translation and ecology in the age of the Anthropocene[M]. London,New York:Routledge,2017.
[27] 武立红. 中西生态翻译研究2.0范式之同名异质:兼《生态翻译:人类世时代的翻译与生态学》述评[C]//吴江梅,鞠方安,彭工. 现代外语教学与研究(2020). 北京: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20:320-326.
计量
- 文章访问数: 144
- HTML全文浏览量: 27
- PDF下载量: 581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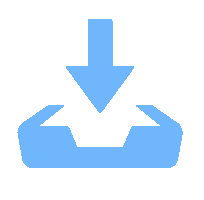 下载:
下载: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