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bstract:
The American ecocriticist Timothy Morton defines global climate change as a hyperobject, which cannot be directly and locally observed by common people because of its super large space-time scale. Climate Fiction (Cli-Fi) came into being against this backdrop, showing to its audience what cannot be intuitively presented by data and graphs often used in science, making imaginable the unimaginable. Besides its ecocritic perspective for all species and the entire ecosystem, Cli-Fi also embodies cosmopolitan and feminist dimensions. As the latest development of eco-literature, Cli-Fi has drawn wide public and academic attention since its rise in the early 2000s.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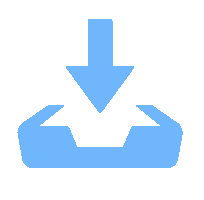 下载:
下载: